作者|相羊
1
家乡到处都是皮肤黝黑的野孩子,淌河水、捞虾米、偷拿爷爷捞鱼的网子去抓蜻蜓,这些都是我们午后必须做的事情,如同上学一样,这些都发生在水边。
蚂蝗、竹叶、水藻、石头。
只管踩上去,享受一个下午的清凉。
这是条汩汩流向大江的小河,它是最终会遇见大海的,老人们告诉我们,即便他们没见过大海。
我们也一样没见过海水,大海大概也不过这条小河的美丽。
它把苍天的剪影留下,留给我们。
以前就是那样,在晴天,它是大地,是漫行的天空。
它就在我们身后,赤诚地望着我们的背影。
可能从太古就开始,可能从我出生起才开始,我希望是前者,这样我才能有更多想象。
好像那些家中空落落的老人家一样,在秋日坐在家门口,望着来往的时间,没几个人去看看那些美丽的眼睛。
2
“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苦痛。
“大家讨厌苦痛吗?讨厌。
“但是大家依旧追逐着。”
我很讨厌这段话,即便我无法完全理解,但是我讨厌,深深地讨厌。说得实在没来由,可恨,谁会去追逐苦难呢?
我把书塞回书架,心里感到这是本多么荒诞和没头脑的烂书。
什么是“苦难”?死亡是“苦难”吗?死亡在书上被人陈述了那么多遍,那究竟哪种是真正的死亡,哪种是真正的苦难?
我长长沉浸在别人看来故作高深的思考里,这几乎成为了我的习惯,不认识我的都觉得我开朗,认识我的都觉得我阴沉。谁认识我?
我并不喜欢,这种思考让我头疼,让我不快乐,这……是苦难吗?
我从老师的书房跑出来,太阳还高高站在山头上,河水把山和霞光都融化在水中,春天已经过去了,夏天可真热,但是我并不觉得苦。
3
身上使不上力,烦躁,白茫茫又沾着些灰尘。
妈妈在叫我,要我干什么呢?
我醒了过来。母亲站在我的床边,声音里鼻音明显,有一滴水落在我手臂上,我花了许久才明白过来,妈妈说的“爷爷走了……”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是爷爷要去哪里旅行了,但是他又为什么要去呢?
他不是昨天才出院吗?他才刚刚回到家里,昨天他还说要和我去河边钓鱼,鲫鱼都长大了,我看见透明的水中,那只鲫鱼一动不动。
爷爷走了,爷爷确实是走了。
爸爸看起来像个小孩,和我一样在哭,他应该也和我一样希望爷爷还能走回来。
我真希望,我还没醒。
那个上午是漫长的,从我的眼泪流完开始,好像一切都变得透明了,爷爷的身体,整个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结果是都变得晶莹剔透。
爷爷的水晶棺是透明的,长明灯的火焰是透明的,他们的声音是透明的,风好像也是透明的,河水都被鲫鱼搅浑了。
A
当我回到公寓时,李世辰睡了,我把客厅灯关上,尹渥还在自己房间里做着一些东西吧,光从门缝中流出。我小心翼翼地踱回房间,窗帘还维持着早晨的严密,我拉开,是零碎的灯火,只有远方的夜幕还透亮——一会儿睡前我还得拉上——我庆幸的是,至少透过这扇狭窄的窗我还能看清大熊星座。在外的苦闷与疲惫让我无心于其他的事情,我瘫在床上,撇头去看窗外,想起儿时只有月光描摹的山野,城市的天际线多么灿烂啊,这是人类创造的伟大,一个畸形的伟大,潜藏着令人萎靡的因素,至少我已经萎靡了。
房间门响起一阵轻轻的敲击声。
“泽哥,应该还没睡吧?”
我打开门,是尹渥。他扶着门框,头偏向一边。
“这么晚你还没睡呢?”
“刚写完论文,”尹渥的头发前阵子嫌太过杂乱已经都剪去,整张脸的疲惫就更加清晰了。我们都是疲惫的人。
“怎么说?”
“吃点夜宵去不?”
我其实不想去,我不饿,况且夜宵又是一笔钱,但我不忍心拒绝他。尹渥,人如其名,家境优渥,不然身为一个大学生,他该老老实实待在宿舍,而不是和我们这些社会人士待在一起。他从小身在大城市,生活体验某方面上比我们多得多,通音律,偶尔还写点小诗,谱些曲子,活得太文艺,飘飘然的一个人,我真希望他能一直这样下去。
“行啊,还是那家大排档吧。”
4
“肖林泽,你写的都是啥啊?”
“故事啊。”
“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写的真的这么差吗?我还为这篇故事画了好多图画,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吗?是我写的太差了吗?我感觉眼睛胀,我绝不会哭。
“写着开玩笑的!”我真不该给他们看的。还是多读书吧。
夏日午后阳光灿烂,斑驳闪耀,处处都在发光,大地在夏天最像一位天使。
B
“你今天喝吗?”
“不喝了,明天还得上班。”酒精和我不搭。
“我明天没事了,论文写差不多了。”他抿了一口塑料杯里的琥珀色液体,泡沫沾在他的上嘴唇上面,“麻烦泽哥你扶我上去了。”
他狡黠的微笑看起来像个小孩子。
“得了,你也少喝点。”
“在说吧。”
这句话之后,我们就没说什么话了,只是伴着灯光咀嚼着那些油腻的肉。他喝下一杯又一杯。
“哎哎哎,干嘛呢,受刺激了?”
“口渴……”
“你注意点,别瞎整。”
“泽哥,”他的声音早变了,变得模糊,分辨不清他的心情,“你平常想家吗?”
“想家了?”他身后烧烤摊的廉价白炽灯晃得的难受,“你家离得近啊,常回去看看。”
我说的很云淡风轻,没有直接回答他。家嘛,南方的群山,明亮的草坡,还有清凉的雨水,我怎么可能不想。
“我不想家,一点都不想,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他确实不是那种会想家的人,他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去旅行,往往又是一个人,黎明时分唐古拉山脉的雾气蒙住金色的雪峰,云南谷底秋沙鸭击水而舞,上海外滩上风力发电机慢慢搅拌着夕晖与咸涩的海风,这些好像都没法满足他,像是个无忧无虑的李白,像是个惆怅孤独的李白,像是个年少轻狂的李白。尹渥想的很多,说的很多,以至于有时候我和李世辰会觉得烦,但是他今天的话都很简短,像是藏了很多东西。还有一种经常的情况他谈得比较少,就是谈起家,他不会主动谈起,即便说起他也会很简短,但是并不有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今天却主动说起。
“我想家,很想。”
他没说话了,只是低着头喝下又一杯琥珀色的光,我们沉默了许久。
5
我下次回来会是什么时候?
我知道,之后的日子是漫长的,县城和家的路途又是漫长的,我真希望我不用离开。大巴在盘山公路上颠簸,这一条山谷,到那一条山谷。
雨和阳光交错着落在车顶,车里的汽油味和尾气味令人作呕,空气又是潮湿的,但窗外却都是美丽的风景,美丽到我变得渺小。
上这辆大巴起,我好像就被迫要在这狭小空间里完成一次蜕变,一次糟糕的变化。
县城高中,真的就那么好吗?在镇上为什么就不能考上大学呢?
我的书包里没有书,都是衣物,母亲在一旁看着我,我突然想起,我要远离母亲了,祖母和父亲也是。
我不喜欢哭,即便被河边的石头扎破了脚我也不在乎。
我想起田里的甘蔗,还有橘子树,他们都长高了,而我还是那么矮。如果家里还像以前一样种着棉花,是不是会更美丽些?
“窗外都是桉树,都是这几年栽的……“妈妈说。
C
“你啥时候回家?“这句话有些没来由,让我摸不着头脑,我一年中回家,永远是那些日子,清明、五一、国庆、过年,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国庆。”
“我是说,回去,不再回来了。”
“怎么可能不回来,让我饿死吗?”
“人生很多种活法。”
“对,很多种,但我只认识这一种。”
不知不觉,桌上的东西已经吃完,只有他的啤酒还剩了半瓶。
“我们走走去吧。”
“去哪?”
“老地方。”
他说的是跨江大桥。
6
高考结束了。
我很开心,一切都到头了,父亲母亲都在考场门口等我。
他们在笑,我也是,那么多人,我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
夏日灼人,江水清澈,我把手深浸在江水里,想洗去尘烟与汗水。
老房子在彼岸,深沉如太古。
今年,它们将被拆除,连同那些枯草,
又一次,我意识到,我回不去了。
不久,我就将远行,飘向未知。
我愿在那里,我还能面对春水,想念。
……
我回到镇上,许多事物,我已认不得.
家后面,已成了整齐的桉树,它们隔开一畦畦的田地,它们近几年才栽下,却已然有两个我那么高了。桉树后,是我的河水,在瘦高的树干间,闪耀着碧蓝的条带,我还认得。对岸是绵延的山丘,和不眠的雾气。
镇上的人和事都已不像以前,但是我庆幸,这里还有河流。
D
夜里的河水模糊不清,只有驳杂的霓虹散乱在岸边的波纹里。身后是汽车的轰鸣,好不聒噪。
“夜晚总是那么亮。”今夜天上无月,有的是几颗零落的星,倔强的大角星是其中之一。
“泽哥,我记得我刚刚遇到你的时候,你写过一篇文章,你还记得吗?”
“我总共就写过那几篇,屈指可数。”
“是啊,但是那篇之后,你就没再写过了。”
“那篇啊,那篇怎么了。”
“我最喜欢你那篇,像个高中生,像个还有天真的上班族,像个诗人般浪漫。”
“别逗,我没有什么水平,写的什么也不是。“
“谁说的?“
“出版社,从来没人收我的稿子。”
“你在写那篇文章时不是早知道了吗。”
“正因为明白,才无法接受。”
“你现在不是接受了吗?”车道上打来的远光灯不断在尹渥的脸上闪烁,如走马灯一般,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他并不在我身边,而是我回忆的一部分。
“什么意思?”
“接受了现实的苦难,并追求它,好像,你从小便生于其中。”
“我从没有接受苦难,我每时每刻都在挣扎。”
“证据是什么?”他猛喝一口手中的的酒,不看着我,“从你停止写作开始,你就成为了世间苦痛的一员,走向了荒原,成为了无止息的转蓬。你还欣然如此。”
“没有人会追求苦痛!”我痛苦地低吼。一辆车从我身后飞驰而过。
“那就证明给我看,如同我学着你的那样!”他手脚轻盈地翻过栅栏,一跃而下,飞入破碎的江水,身后是他的欢呼。
我怔在原地,看着他跳下,不明白他的意思。我大声呼喊他的名字,没有回应……身边都是嘈杂的人声……我的身体驱使我一齐跳入江中,但是一万只手抓住了我,将我驱离那片没有光彩的江心。
7
傍晚,他被告知自己失业了。现在他感觉自己一身轻,近似一片飘零的银杏叶。
他打开手机,锁屏上映出张张红润的笑脸,画面中的青年学生们手持琥珀色的饮品,他本人站在旁边看着同学欢呼雀跃,偷笑画面中的一幅幅窘态,图片拍的很模糊,像是漫漶了,但是每个人的欢意仍然清晰,照片中的他面对着同学的劝酒玩味似地说了句:“有梦想的人不陶醉。”
“十二月十六,腊月,18:03.”时间恰好盖在他们脸上。
黄昏走近,天边的颜料被打翻了,有的云霞过于红艳,有的却如此深邃,不过它们都拥抱着同一片苍穹。
他跨上了自行车,高中毕业时父亲送的,就在那一个夏天,它曾载他行过数不清的山路,轧过各味的土壤,而今车链已有些生锈了。他踏上踏板,“嗒”的一声后他没再回头看一眼公司高寒的大楼,穿插过人流,驶入车流,摩挲着笼头磨损的一端。
他觉得自己手冷极了。毕业后,他变得越来越少开口说笑了,在工作与生活上,这让他过去的开朗活泼显得虚伪,像是刻意在维系某些脆弱又不安的关系,但实际上真正脆弱与令人不安的只是一个人面对的生活,从百无聊赖到包围他生命的陌生与冰冷。当一个人想捂暖另一个人的手从而可以彼此握手时,热心的人需要分享自己的温暖,现在他大多的热量已遗存与学生时代无数沾了水墨的手掌上,面对望不到头的生活,他的温暖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落日余晖在他脸上抹上酒醉似的红晕,即便冬日寒冷。
他在城市一个个拥挤的路口穿行,驶上了大桥。江上金光斑驳,听不见水声,风很大,把那些亮丽的文字都磨花了,他的影子卧向光相反的方向,好像渐行渐远。
桥上曾有人从此跃下,自愿的,但他的记忆与跳河者的身躯已一同被冲去,在那个人跳下后一切似乎也没有变,像一道伤口,被河水的温度所麻木的伤口。看着不息的河流,他想,人们跳入一条条河流,但很少有人真的热爱冰冷的河水,相反,他们为了跳出一条条汹涌的河流而跳入了又一条大河。
他看见桥路旁早早便有了醉酒的人,那些人瘫软,晾晒在栏杆上,念叨听不懂的胡话,像一面战败之人的战旗,又像海滩上无数的海星,他想去帮忙,想做点什么,想做点至少他还能做到的,如果不这样的话,在朔风下,也许这些旗帜不知何时会被时光吹入江河,一路入海,沉寂在某处。他刚停下车想步上前去时一个女人从旁快步走来,手上拿着手机,盯着那个醉汉叹了口气,嘴里念叨了几句,接着便吃力地背起醉汉离去。他也骑上单车走开了。
天空渐黯了,城市的天际线也明显起来,林立的高楼间,霓虹漉染,每份色块在散光的双目中都巨化了,他仅是那无垠光影里的一个斑点,是油画的一滴,有可能是绝画的点睛,但很显然不是。
一路上,他的鼻根攒满酸楚,眼眶却始终没有下雨,“不要哭”是从小大人们对他说的一句话之一。汽车在鸣笛,人声意外地稀少,他闯入更为繁华的城区,人声与呼呼风声如雨点迎面打来,霎时间占领了全部的空气,又忽地蒸发了,一片连一片。
十字路口从来不接受任何祈福,城市殷红的眼睛闪烁着警戒的信号,这信号能传递很远,同时也不带丝毫温度。他将车停在斑马线前,天空正加速消耗剩下的光芒,人流在斑马线上或快或慢地走,母亲牵着孩子的小手,学生们推搡跑过,余下阵阵欢腾,上班族提起深色公文包急匆匆地走,老人携老伴步履蹒跚,他想去听到一些东西,但是他耳鸣的嗡嗡声充斥了此处。
他摘下自己的眼镜,他把上面水雾揩干,拉远了距离去透视这座城市,黛赭、丹红、绛紫、金黄,似乎这偌大的城市囊括下了所有的光彩,但又全部分散开,无法并作一道洁白。绿灯亮起,身后铁皮的呼鸣赢过了他的耳鸣,他再度出发,将眼镜别在已经松软的衬衣领口,继续在一片不可名状的世界中骑行。
左拐,直行,右拐,钻入小巷,进入另一开阔的未知,冬天的风像是要撕裂他冻僵的面颊,眼眶不自觉地流下风里易逝的晶莹。他决定停下车。
他打开口袋中手机,他不知是否该庆幸手机上消息通知干净得一条烦人的广告都没有。他现在想有个人与他说说话,他翻看着通讯录,几个同事、客户、父母与亲戚以及许久未联系过的同学,还有一个,他自己,名字后面还带着一串“——文豪”,他呆呆地笑了,风未曾停息,眼眶却始终干不了。他拨通了一个“死党”的电话,
“嘟……嘟……”他期待一个带点孩子气的声音会在稍后埋怨自己的对方对自己的打扰,然后聊起逝去的日子。他开始一点点拾起记忆角落的碎片,汽车飞驰而过的声音,难闻的尾气,人群的吵闹,拼凑出他初到这座都市的图画:背负着同学们的祝福,高远的志向,他想成为一名作家,改变世界,他期待为人们点燃烛火,他不喜欢城市的冰冷,喜欢原野的清芬,他不喜欢黑夜的喧嚣,喜欢白昼的静谧。他一边透过落地窗打量着城市,坐在那个奋力争取来的办公位,一边书写着自己在缝隙中的生活。
悄悄地,雨水摸上他的脖颈。他打了个寒颤,手机从手中滑落坠地,跌入了排水沟,他连忙蹲下去拾起,排水沟里污水浸湿了手机,墨黑的屏幕映照出他清瘦的面庞,扑朔的霓虹衬起一张陌生的面庞,他试图去抽取关于学生时代自己的画面,但他与那段岁月早已隔上了一层黑色的薄膜,透过薄膜看见的一切都渐褪了鲜明的色彩,好陌生。
雨逐渐大了起来。现在他戴上眼睛镜框。鼻夹是凉的,寒冷刺入皮肤。他没有伞,他在城市的街道间推着自行车随意地漫游,让雨水拥裹住他。他走过一家商店旁,里面林林总总装满了各色的商品,橱窗里是几个可人的玩偶,灯光的暖色调柔和得没有一点棱角,而窗外的雨打在他身上则粗糙得多。
雨天他最爱的一件事之一就是看细小的雨珠挂在他那把透光的深紫雨伞上,让或象牙白或昏黄的路灯将灯撒过伞与雨,雨幕下,他的私人穹顶上显出了一片纯净星空。而另一件事就是淋雨,在无人拥抱他时去拥抱天空的一部分。
生活于他无非是一场大雨,学生时代他总打着伞,雨水会破碎在穹顶之上化成清晰可触的星河,当他为自己在倾盆的雨滴里曼舞时,会有人看向他,但被雨幕过滤后的眼光永远是柔和的,于是他无比轻盈;长大后,他的雨伞落在了家门里,雨仍未停息过,每个人都行走在灰蒙蒙的世界,已经很难一身清爽地静望一处灯光,一滴滴雨水从各方天空降下,汇成溪流于钢筋水泥的罅隙中不息,时而激荡,但却难以溯源,水的推力很大,每滴水都在彼此的推搡中无法驻足。
街道上人潮汹涌,斑斓的雨伞编织出的绣花平铺在雨水倒映的另一个世界上,他在其中突兀。他感觉雨水让他的身体同注铅一般沉重。
他尝试着打开手机,庆幸雨水还没让一切变得更糟,点开音乐软件,播放起歌曲,戴上卫衣的兜帽,塞上耳机。他很喜欢摇滚,喜欢披头士乐队,喜欢列侬,以至于他会在历史课走神时在《拿破仑法典》书影的图片下写下“Penny Lane”。
“便士街上有个理发师在店中贴满了照片(In Penny Lane there is a barber showing photographs),
“认识其中任何一个人他都会自豪(Of every head he’s had the pleasure to know),
“来往的行人们(And all the people that come and go),
“都会停下问好(stop and say hello)……”
“……便士街总在我耳畔萦绕,在我眼前浮现(Penny Lane is in my ears and in my eyes),
“就在湛蓝天空下的市郊(There beneath the blue suburban skies)……”
歌曲放到一半时手机就电量不足关机了,他却仍然带着耳机,在路灯下静静推车,眼镜上早已挂满水珠。路上到处是打伞的行人,他们的伞就像一朵朵花开在这个嘈杂的雨夜,有些沉郁,而后在晴日里凋零,再然后雨又至,镜片上滑下的水珠后面,他第一次从心里看到了这样的轮回。但晴日里草地上的花不是在灿烂地开放吗,或许他们代替了那一把把伞吧,他想着。
不知不觉中他走到了公寓楼下,他抬头看向出租屋的阳台,黑黝黝的。他记不起自己为生活与梦想奔走了多远,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他都一败涂地了。他想象,自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楼道间摸索上楼,推开房门,打开前些日子刚修好的日光灯,脱去湿漉漉的衣服,冲个热腾腾的澡,再次一身轻,看向窗外茫茫的高楼大厦,望不见任何尽头。他拾掇起一片秋天遗留下的银杏叶,在其上写满生活,但是黄叶太轻,笔墨过重。
——肖林泽《轻》 献给自己
8
18岁那年的元旦,我第一次遇见了海洋,黑暗的潮水在海雾的暗沉里涌动,我明白了,这就是春水的归处。
寂寞的海风刺激着我的身体,激动着我的灵魂。我的身旁除了几个放烟花的游人外,只有涛声。洁白的海冰像是一处岩壁,横亘在我与海水之间。身后是漫漫滩涂,十分钟之后,我开始想念碧蓝的春水。那条河流并不清澈,但是映出了碧蓝的上空,它把苍天的剪影留下,留给了我们。
18岁那年,月高悬海上,四处烟火肆意,而我,在无人的夜里,烧掉了海洋。
E-End
夜晚的打捞工作,几乎是很难得到结果的,一直到黎明,我才得知他们找到了尹渥,但是他已不在这里了。警察问了许多关于他的事,但是我又知道什么呢?我始终无法明白,他为何跳下去。一直到晌午,我才打电话告诉李世辰这件事,我没法看到他的脸,我说出这个消息时,他沉默良久,只有一些不规律的呼吸声在回答我,然后他便挂了。
尹渥的父母第二天便赶到了,满脸惊惶,面色苍白,我听护士说,他们在太平间哭了很久。这一天是周四,李世辰和我都没去上班,这是没法整理好心情的,即便我从那晚后,就没再哭过。李世辰看着比我憔悴多了。是啊,我们都爱着这个年轻的朋友啊!
后一天,尹渥父母来到我们合租房。尹渥继承了他们的容颜,当我见到他们时,我总希望尹渥也在。他们站在一起,搀扶着彼此,两个人都在五十岁上下,脸上是忧愁的沟壑。他们和我们询问起尹渥的事,我面对着他们无地自容,我始终认为,是我导致了尹渥的冲动。那天,我们真不敢出去的……他的父母在我们面前竭力做着一副庄严的模样,但是这副伪装完全没有意义,他们好像两根绷紧的弦,随时都要断裂。我想到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尹渥原来也是一根绷紧的弦。他们似乎很爱这个儿子,脸颊上透红的泪痕刺痛我,我想扑在他们脚下祈求原谅,我希望我也一并跳入水中——多么快意的逃避与解脱啊,懦夫!
我期待他们会谈起尹渥的过去,但他们谈到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好像,尹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孩子一样。我得不到我要的答案,他们也是。他们把一切都归结于这座该死的城市和酒精。
他们临走前带走了尹渥所有的东西,那里面一封遗书也没有,那些尹渥房间里整整齐齐排列的书本被打乱、打包走了大部分,尹渥的父母留了几本给我们——一本萧红的《呼兰河传》、一本霍夫曼施塔尔的《傻子与死神》和其他我们从未读过的论文集,它们都崭新而美丽。尹渥留下的东西,令我惊讶的是,连一篇手稿都没留下,那些他夜里曾读给我们的诗,全部散佚了。他的诗,我这才醒悟过来,他的那些诗,那些朦胧里的情绪,那些偶尔的感伤——在这个人人感伤的时代,我们只把那认作平常——早被吐露在我们面前,只不过我们让它们于生活中全漫漶了,只有尹渥一个人,压实在了心里。
我来自世上不存在的地方
留在世上重复的风景
……
我的一双脚有自己的理想
我的双眼看见了悲凉
这是他曾吟诵的几句,如今我已记不起太多。
尹渥的房间空了下来,李世辰站在窗前,远远地,那条河穿过整座城市,正想着更远处流淌,那里就是尹渥的新房间。
“我们该怎么办?”李世辰低声说。
一直到多年后,我才在我曾借过尹渥的一本书中找到一张泛黄的明信片。
我走过昆仑山山脚,恍惚间脑海闪入一条高原的经幡,有一阵风怒号,我哭了,像往常一样,有一只蛱蝶在脚边翩翩,我不想回去了,我的父母,我将投入我更广阔的母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睦。
2014年11月15日
又一年春天,我和李世辰站在跨江大桥上。
“我们来看你了,尹渥。”李世辰站在我身旁,“你泽哥今年就回家了,以后这座城市只剩我了。
“林泽,你也说几句啊。“
“再见吧,尹渥。“
“有时觉得你话少清净,有时觉得你话少烦人,这种时候还憋不出几句话来,亏你还是个高材生。“李世辰的声音渐渐不稳定起来。
“对不起。”
“你道歉干什么?你又没做错什么,我们谁都没做错,尹渥也有自己的原因,现在他已经自由了,愿他安好吧!”
“愿他安好!”
“回去之后,也要联系哈。”李世辰看向我,苦笑着,“有什么话要捎给渥的随时告诉我,我替你转达。”
“要是真有,我也得自己回来说。“我笑了笑,带着苦涩。
“好啊!到时候我也得听听。好了,你走吧,到了报个平安。”
“好……”
我坐上了回乡的车,我不知道我会在待多久,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找到自己的春水,我做出这个决定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带着某种毁灭的因素,就像尹渥一样,但是,我会继续活下去,这是我的选择,我会继续生活下去。
一篇残缺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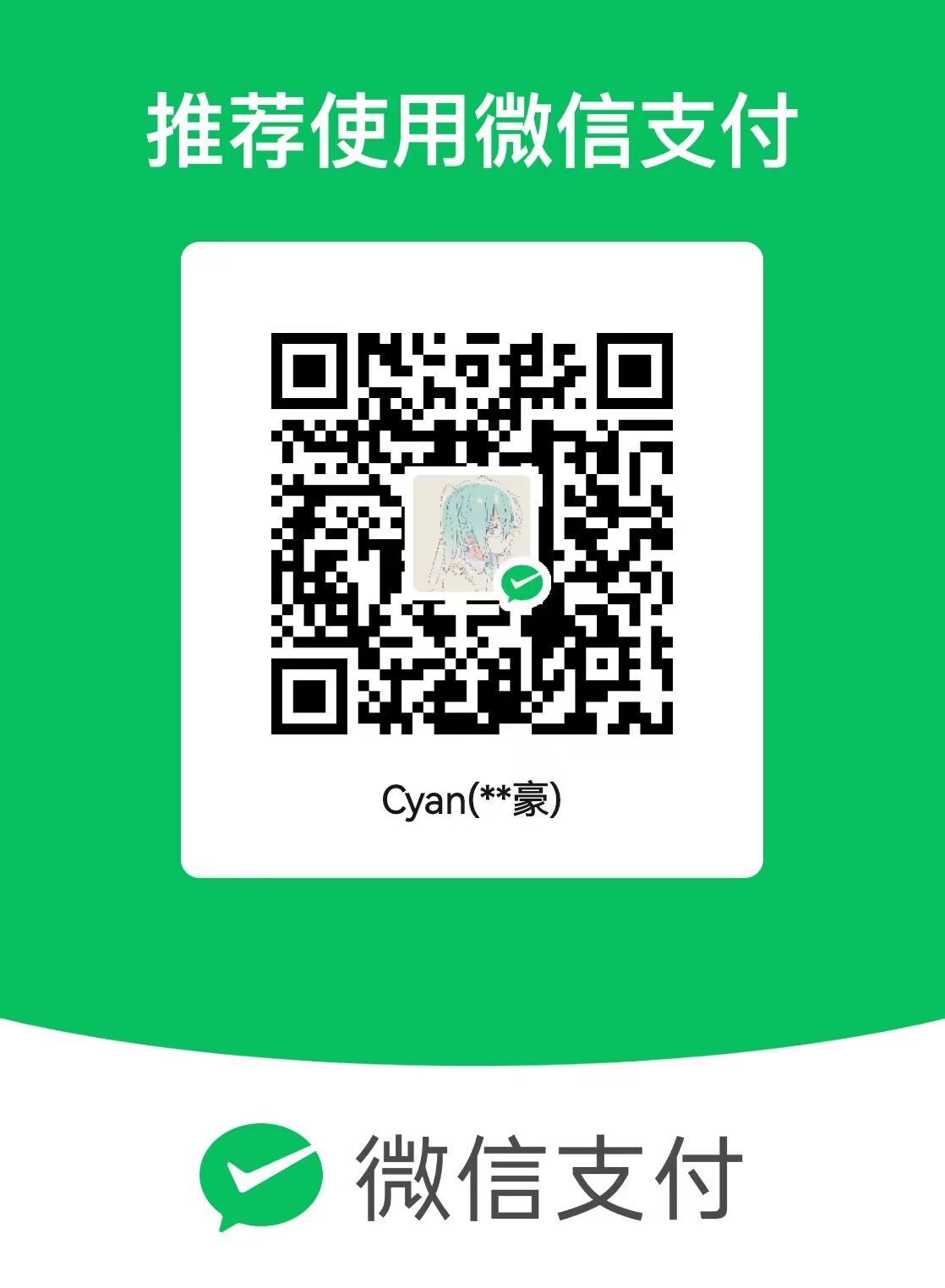


我嘞个大神啊
给我打赏
赞赏博主谢谢喵